孟德斯鳩迷惑了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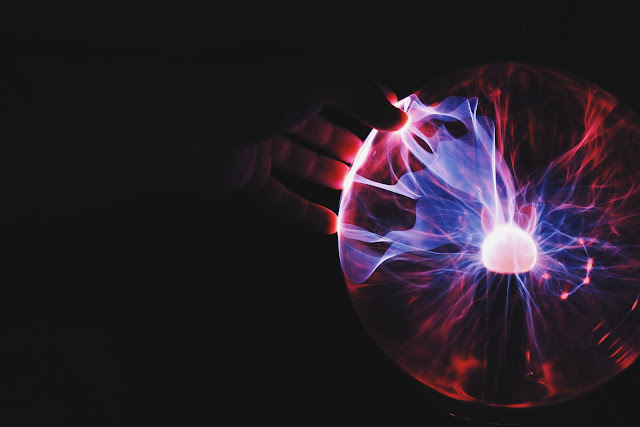 |
| (Photo by Ramón Salinero on Unsplash) |
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在啟蒙運動時期,那可真是太好了。一片「中國熱」,從穿衣、喝茶,到思想、藝術,跟我們現在崇洋媚外一個樣。
可是18世紀中葉以後,就翻轉了。歐洲變成自由、進步的,中國則停滯於君主專制社會中。
這就是孟德斯鳩的影響。
這位法國鈔票上印著他頭像的學者,於1748 年出版了《論法的精神》,倡之於前,黑格爾等人繼於其後,漸漸塑造了一般社會認知。
這樣的認知,最有趣的地方,不只於此,而更在於它還變成了近代中國人自己對於中國的認知。——因為,引進西學時,就引進了這一套「罵中國」的論調,所以大家漸漸都學會了。
一、君主立憲者的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最早被介紹到中國,是1899年梁啟超《蒙的斯鳩之學說》一文。1901年梁氏又發表《立憲法議》。一方面介紹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之觀念,批判專制政治,一方面也藉機提倡君主立憲。
在這樣的論述情境中,梁啟超完全接受了孟德斯鳩對中國專制政治的批評,認為「泰西政治之優於中國者不一端,而求其本原,則立法部早發達,實為最要著者。」
1913 年嚴復譯《法意》出版,附有按語330 則,是他所有譯著中按語最多的,影響尤大。
嚴復對孟德斯鳩之學說並不盡數贊同,例如兩人的宗教觀即差異甚大,嚴復根本視宗教為迷信,更擔心洋教會擾亂中國的社會,所以說:「孟德斯鳩生於法民革命之前,故言宗教之重如此。假使當一千七百八九十年之間,親見其俗,弁髦國教,吾不知其言又何若也。」「他日亂吾國者,其公教乎!」
他又批評孟德斯鳩根本不懂佛教:「 孟氏以此攻佛,可謂不知而作者矣。」推此意,嚴復也必不會同意孟德斯鳩基督教精神與自由最能相合的議論。
嚴復又說孟德斯鳩對中國社會禮俗之理解也頗有錯誤,如說中國因男女防閒極嚴,所以不可能有私生子;或說中國人善欺詐;中國禮俗久而不變等等,嚴復都不同意。孟德斯鳩以風土論斷民性之論證方式,嚴復批評尤多。
對於禮的問題,嚴復更與孟德斯鳩不同。嚴復強調禮,故有一按語,舉曾國藩為說,云:「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又說「歐洲之所謂教,中國之所謂禮。」
正因為如此,孟德斯鳩大力抨擊東方專制主義起於家庭內部之奴役,而家庭內的奴役又以幽閉婦女為其特徵時,嚴復卻大力主張嚴男女之防,不但為古人嚴男女之防辯護,稱此制旨在保護女性;又說一夫多妻(其實是一夫一妻眾妾制)對男性造成的痛苦更大於女性。同時,還正面藉孟德斯鳩提倡女性貞操之言,主張守貞才能真正自由。
守貞才能自由,這種說法顯示了嚴復的自由觀非常特殊,起碼不同於孟德斯鳩,所以他又說:「西士所急者,乃國群自繇,非小己自繇也。求國群之自繇,非合通國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愛國,人人於國家皆有一部分之義務不能。」
認為國群自由重於小己自由,而自由又關聯於義務,是他與孟德斯鳩迥異之處。
兩人還有其他許多不同。然無論嚴復與孟德斯鳩如何不同,孟德斯鳩對中國屬於專制政體的批評,嚴復基本上是接受的。
他曾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 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
可見他對中國專制之論斷,甚有會心,不但頗為契合,更因所處時局之故,發言較孟德斯鳩還要激切。
他說中國本來也有君主立憲的精神,但這種精神到秦以後就喪失了,人民基本上只是奴隸,所以與西方之君主制不同。
這裡引申孟德斯鳩之意,揭發中國專制的殘酷面,且關聯著當時中國淪為次殖民地的「五洲公共之奴」情境來立論,言辭帶著感慨痛憤之情,足以令人想見他引薦孟德斯鳩此書到中國,是具有強烈的現實性的。其批判專制,亦即欲以此開啟民智、建立君主立憲之政。
二、革命者的孟德斯鳩
君主立憲的對立面,是革命者。這些人醉心於民主自由、嚮往法國大革命、主張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只會比梁、嚴等人更甚。孟德斯鳩以中國為東方專制主義之代表的論述,當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人詮釋中國古代及清末民初當時存在的社會的典範。
而且近代中國政體變造的過程又極長,並不因辛亥革命成功就結束了。辛亥革命廢除帝制之後,因袁世凱準備稱帝及北洋軍閥割據,而有護法等役,此後一直到成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等等,都屬於由帝制轉換到民主政體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過去均處於必須揚棄的,批判並揚棄它,才能順利完成憲政改革,成為社會民眾普遍的認知。
同時,帝王專制時期雖然在形式上已被改變了,但專制政體的精神,亦即「恐怖 — 服從」的邏輯,大家都認為還沒打破,所以民主憲政的建立才會如此困難。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一連串反省國民性、改變中國人奴性的思想文化活動,也都呼應著孟德斯鳩對中國政治、國民性的論點。
這些情形綜合起來,就形成了孟德斯鳩式中國觀典範長存的結果了。
三、憲政主義者的孟德斯鳩
近代中國之改革,又與留學歐美之知識分子有絕對之關係。他們有著與孟德斯鳩、黑格爾以降一脈相承的東方觀,也是絲毫不足為奇的事。
其中,本諸歐西民主憲政學說,對中國傳統政治進行徹底批判,以促進民國憲政之建立,憲法起草人張君勵的《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一巨冊尤可視為代表。
此書旁徵博引,反駁錢穆中國君主制未必即為專制之說,證成孟德斯鳩以中國為專制政體之論案,可說是孟氏最雄辯的闡釋者。此書初在《自由鐘》連載,後來結集成書,長達650頁。與張先生見解類似,反對錢穆之說者,尚有徐復觀。
這當然不是說張君勵之說即為孟德斯鳩之說 — — 張氏之見解不盡同於孟德斯鳩,一如梁啟超嚴復之不盡同於孟德斯鳩 — — 而是說一種學說的接受史往往與接受情境有關。
 |
| Photo by Oskaras Verbickas on Unsplash |
四、由歷史發現歷史
孟德斯鳩的東方觀,由於其時代因素,逐漸在各種論述中脫穎而出,打垮了讚美中國的各種說法,占據典範地位,而發揮其影響力,影響了西方的東方論。這種影響關係,並不是一個個體對另一個個體所產生的影響,而更是一個歷史脈絡、認知情境與人所發生的意義關聯。一種講法,是因為鑲嵌到這個脈絡中而被理解的,其理解也與這個整體脈絡有關。
無論孟德斯鳩的理論在純粹法學意義上有何價值,或在對法蘭西當時政治環境之改善方面有何作用,它關於東方專制而歐洲自由的論述,放在18、19世紀歐洲殖民主義擴張的情境中看,當然具有那個歷史脈絡的意義。
正是這個脈絡,使得歐洲人不再採納「聖善天堂」的東方觀,而逐步將遠東的中國視為「邪惡帝國」,繼而再視為落後的「黑暗大地」。陽光雖曾照耀過,但沉滯而無進步,永遠停留在童稚時期,以致啟蒙工作終不可少。
晚清民初的啟蒙運動,乃因此而必須是引進西方理性之光、敲響自由之鐘、建立民主之制。
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中,中國人遇見了孟德斯鳩,並接受了他對中國的貶抑,誠懇地以懺罪悔改之方式,發現自己原來只是奴隸。
在這個脈絡中,孟德斯鳩所提供的,只是一幅基本圖像,略具山川形勢之大貌而已,許多地方是煙雲模糊或逸筆草草的。要接受者各以其感受於時代者穿插點染補足之,才終於成為一組混聲大合唱。
要針對這樣的大合唱來指明其基本旋律已然失誤,並不容易。仍處在民主政制改革進程之中的知識分子,極少人能跳脫出自己身處的認知情境,反省自己對東方、對中國的觀念究竟從何而來,並以「知識還原」的方法,重新思考我們理解自我的歷程。
五、錯誤的孟德斯鳩與專制東方
在孟德斯鳩的論述中,法制的西方,與那將禮儀、風俗、宗教、習慣混為一談的中國,是一種明顯的對比,而且中國這種情況還被他當成特殊型態來說。
可是真正考察西歐法律史,就會發現:法律與宗教、道德、習慣等等區分開來的特徵,雖可見諸羅馬法,但卻並不普遍。11世紀前通行於西歐日耳曼民族中的法律秩序,並沒有表現出這些特徵。
據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的研究,11世紀左右,法蘭西、英格蘭及歐洲其他地區也都沒有這樣的區分;是要到1080年羅馬法被發現、1087年歐洲大學中建立法學院後,才逐漸依羅馬法而發展出各國法律與宗教、道德、習慣區分開來的體系。
也就是說,羅馬法所顯示的這種特徵,可能才真是特殊的。孟德斯鳩處在西方近代法律傳統構建已成的時代,又以羅馬法為典範,把中國跟其他民族大抵類似的情況視為特例,大加譏評。以特例為普遍,反謂普遍者為特例,實在不恰當之至。
孟德斯鳩又將東方專制社會形成之原因,歸諸地理氣候等,自然也是不能成立的。對於中國歷史及法律狀況之理解更是頗多可商。因為整個論述是「立理以限事」的,亦即先立三種政體之分,再分別揀摭摘選史事例證以填塞之。
嚴復說他「其為說也,每有先成乎心之說,而犯名學內籀術妄概之厲禁。……往往乍聞其說,驚人可喜,而於歷史事實,不盡相合」,實是一點也不錯。
例如論不同政制下妝奩和婚姻上的財產利益,謂君主國妝奩應多,共和國妝奩適中,「在專制國裡,應該差不多沒有妝奩,因為那裡的婦女差不多都是奴隸」。君主國家,采夫妻財產共有制。在共和國,這種制度便不合適。「在專制國家,這種制度就是荒謬的。因為在這種國家裡,婦女本身就是主人財產的一部分。」
這些都是他的臆測。因為,事實上,被他稱為專制政制的中國,歷來婦女都有妝奩,也都實施夫妻財產共有制。且早在漢律中即已規定:妻子離異時妝奩資產可以全部帶走。後世除元明之外,均沿其制。家庭分財產時,妻家之財也不在分限。
所以婦女在婚後除夫妻共同財產之外,其實還有部分私有財產,這是比西方羅馬法以來更為進步、更能照顧婦女利益的法律。孟德斯鳩那套虛立一理以妄概事例之辦法,在此是完全說不通的。
討論各政體中民、刑法之繁簡及判決之形式時,孟德斯鳩又說專制國家中因為所有土地與財產都屬君王,所以幾乎沒有關於土地所有權、遺產的民事法規,也「完全沒有發生糾紛和訴訟的機會」。可是漢律之中,「戶律」便是談婚姻、家庭、財產繼承、所有權、錢債等等的。唐律「戶律」,以迄清朝「戶部則例」也都對此有所規範。如此,又如何能說中國乃一專制國家?
他講家庭奴隸制時,指的是婦女。將一妻制的歐洲和多妻制的東方對比著說。東方因為多妻,「妻子是時常更換的,所以她們不能掌理家政。人們把家政交給了閹人,所有鎖匙都交給他們,家務事由他們處理」。
這樣的話,可還真是笑話!他不曉得中國一般家庭均無閹人。而且在法律上,中國也一直是一夫一妻制的。秦漢至明清,法律均禁止有妻再娶。唐律規定:有妻再娶者徒一年,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明清律則規定:有妻更娶者杖九十,離異。妻之外,所娶者均為妾。妻、妾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
而且娶妾之俗雖普遍見於民間,但在法律上,娶妾原只准施行於貴族大臣,一直到明律中才正式規定:庶人年四十以上無子者,許選娶一妾。至於妻的職責,就是掌理家政,這是每個中國人原先都明白的事。
在政治方面,孟德斯鳩已對專制政體不應有監察制度而中國居然有之深感困惑,但他若對中國政制知道得更多些,他的困惑一定會更多。
以唐制言之,號稱獨裁專制、權力集於一身、可以不必依法行事的帝王,其誥命不但須要經中書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的給事中、尚書省的尚書丞更都有權封駁、退還制誥。
此制,宋明以降皆沿用之,《宋史.職官志一》說給事中「若政令有失當、除授非其人,則論奏而駁正之」,即指此。這對王權當然會形成制衡。
此外,唐代制度,中書省又設右散騎常侍,掌規諷皇帝之過失;設右諫議大夫,掌諫諭皇帝之得失;設右補闕、右拾遺,則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門下省也設有左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左補闕、左拾遺,功能相同,都是專門職司監督糾正天子過失的制度性設計。
它們與監察機關監督百官者不同。對制衡君王,有比孟德斯鳩所重視的監察制度更強、更直接的作用。
這樣的設計,以現在民主政治的原則來說,是否仍可稱為專制,固然還可有許多爭論,但依孟德斯鳩對專制政體的界定來看,是絕對稱不上專制的。
可是因為受到東方專制論的影響,現今整個東方法學研究,都不斷強調它與專制政治的關聯。
以王立民《古代東方法研究》一書為例。此書將東方法之起源歸為三種類型:屬於宗教型者為希伯來法、印度法、伊斯蘭法;屬於習慣型者為俄羅斯法、楔形文字法;中國法則屬於倫理型。所謂倫理型,無疑與孟德斯鳩對中國法律混糅於風俗禮儀之說有關。其次,該書第四章即是《古代東方法與專制制度》,下分三節:專制制度是古代東方的基本政制制度、古代東方法對專制制度的維護、專制制度對古代東方法的影響。
這樣的敘述,很顯然,是完全立基於東方專制論之上的。所以該書甚至說中國的專制制度已有四千年之歷史。
此書是中國大陸研究東方法最重要的著作,而其所見如此,不難想見此一領域正如何被東方專制論所盤踞占領。故重新理解中國法制之精神,實深有待於後來賢哲。
此外,討論中國政體是否屬於專制,也不能如孟德斯鳩一般,缺乏歷史性之認知。中國皇帝之稱為天子,早在周朝已然。但周天子僅為各部族封國之共主,怎能稱為專制帝王?
魏晉南北朝時期,則是門閥貴族政治,帝王即使想專制,又怎能專制得來?孟德斯鳩將中國想像為凝固的社會,才會以專制來概括幾千年的政治狀況,而不知其間是變化甚大的。
諸如此類,要細談,還多的是,可是僅此即足以說明孟德斯鳩之說無論在方法和論據上都不能成立了。
像這麼樣一個建構在錯誤方法及論據上的東方觀,生於歷史的因緣中,又因歷史之因緣,而成為近二百年來歐洲人與中國人認識中國的基本圖像,有什麼道理嗎?
歷史發展本身,似乎就是它之所以如此的道理。此外,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嗚呼!
…



留言
張貼留言